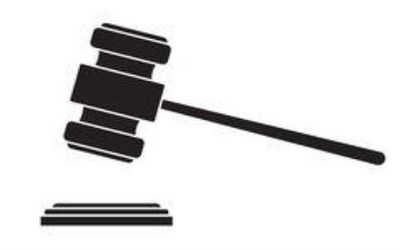清晨六点,闹钟刺破城中村出租屋的寂静。我揉揉惺忪睡眼,挤上开往龙华富士康园区的公交,身体随车厢摇晃,像流水线上尚未固定的零件。七点半,穿过戒备森严的厂门,在更衣室套上静电服——蓝白条纹,千人一面。打卡机“嘀”声响起,一天正式开始。
流水线如银色长河,我坐在工位前,成为其中一个节点。左手取电路板,右手持电烙铁,锡丝在焊点融化、凝固,重复,再重复。主管在背后踱步,对讲机里传来“加快速度”的催促。空气里弥漫着松香与塑料加热后的微焦气味,机器轰鸣是永恒的背景音。我的动作逐渐机械化,眼睛只盯着板子上的绿色网格与金色触点,思维却悄悄飘向远方——昨夜睡前浏览的那个拍卖网站,一支十九世纪的古董钢笔正被竞拍,价格不断攀升。
午休半小时,食堂人声鼎沸。我端着不锈钢餐盘,在角落坐下。手机屏幕亮起:拍卖倒计时三小时。那支笔的详情页在我脑中展开:玳瑁笔杆,14K金笔尖,1890年伦敦制造。我默默计算着时差换算自己的积蓄,手指在油腻桌面上无意识地模拟举牌动作。同事谈论着加班费和周末聚餐,我点头应和,心却已穿过大洋,置身于伦敦某间古老的拍卖厅,槌声即将落下。
下午的车间更加闷热。我负责检测环节,透过放大镜审视每一处焊点。瑕疵品被扔进红色塑料筐,发出清脆撞击声。这种声音让我想起拍卖师的小木槌——同样决定着归属与价值。线长突然拍我肩膀:“发什么呆?这批货赶着出货!”我猛回过神,指尖传来烙铁短暂的灼痛。肉体在此处被规训,精神却需要另一个出口。或许正因身体被固定在流水线前,想象才更需要逃往更广阔的时空。
傍晚七点,加班结束。走出厂房,深圳的霓虹刚刚亮起。我坐在回程公交上,打开手机拍卖直播。屏幕上,那支钢笔的价格停在某个数字,成交槌落下。我轻轻呼出一口气——虽未参与,但全程见证了一件物品如何找到新主人。这让我想起车间里成千上万的手机主板,它们终将流向世界各地,被不同双手握住。某种意义上,工厂也是巨大而精密的拍卖场,只不过这里拍卖的是时间、体力与重复劳动。
回到十平米的出租屋,我摊开笔记本,开始记录今日见闻:车间的温度、焊点的光泽、同事们方言的片段。然后翻开另一本,继续研究欧洲拍卖史。两种生活在此刻交汇——流水线的纪律培育了我对细节的敏感,而这种敏感恰恰是鉴赏古董所需的素养。身体或许暂时困在电子厂,但透过网络,我能触摸到另一个世界的纹理。
临睡前,我再次查看拍卖日历。下周三,一批民国旧书即将开拍。设置好提醒,关灯。黑暗中,流水线的节奏仍在我脉搏里跳动,但耳畔似乎已响起遥远的槌声。明天,我还将是一台合格的“机器”;但此刻,我是自己精神世界的拍卖师,正为那些无法抵达的远方,默默举牌。